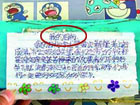父亲去世后,陈忠和组织了家庭会议,他建议把老宅最好的部分分给大嫂,“她这么多年自己带三个儿子,很不容易。”他让两个姐姐先选,自己要了最差的房间,“我不要也行,反正我也不在龙海住。”
大姐夫周宁安是陈忠和的启蒙教练,俩人有三重关系:姐夫、师徒、朋友。周宁安现在住在龙海体委1991年分的房子,客厅的“八骏图”就是小舅子送的,上书“乔迁志喜,弟忠和贺”。
陈忠和快从解放东路小学毕业时,正逢龙海要举行排球比赛,学校便抽调一些喜欢运动的学生组成临时排球队,陈忠和也在其中。从小带弟弟的大姐对时任龙海二中排球队教练的丈夫周宁安说:“能不能把忠和调到你的球队,我也好照顾他。”大姐陈淑贞当时是二中的校医,周宁安也早就有意把忠和调到自己的门下,这样,小学毕业后考上龙海一中的陈忠和被周宁安要到了龙海二中,一边读书,一边参加学校的排球队,这样一晃就是5年。
“忠和特别懂事,姐夫当教练,他就表现得比别人更勤奋,更努力。”周宁安说。
二中的排球场是队员们自己修的,拉泥土是重活,“他一定要当板车头,这是最累的,让他在后面推都不干。怕别人说闲话。”
1977年下半年,高中毕业的陈忠和上山下乡了,他到离龙海市区13公里处的东园公社秋租农场当了知青,除了干农活,陈忠和还学会了抽烟、喝功夫茶,这也成了他一生的癖好。
陈忠和在农场打发青春岁月的时候,大姐夫那边传来了好消息。1978年,福建省准备成立青年男子排球队,要到墨西哥参加国际比赛。晋江人许夕通是这个队的主教练,有一次在从厦门去福州的火车上,许夕通正好和周宁安坐在一起,他问周宁安:“你们龙海有一个陈忠和,我看过他打的几场球,想调他来省队。你了解他的情况吗?”
周宁安一愣,“他是我小舅子,不过他才1.77米,省队?别开玩笑了。”
“我要一个后排防守队员。陈忠和防守和发球好,这就够了,回到省里我就给他下调令。”许夕通说。 很快,调令下来。周宁安蹬着脚踏车跑到农场通知了陈忠和。时值6月份,正是闽南的农忙季节。农场场长挺支持陈忠和,安排他撑船回县城卖鱼和西红柿,以便等候消息。“卖多少算多少,调令一来你就走,我再找人替你。”场长说。
卖了一个月鱼和西红柿,陈忠和还是没接到通知,狂喜变成了心灰意冷。他回到石码镇,再等了一个礼拜,决定回农场,“现在农忙,我却不干活,说不过去。”回农场要经过二中,大姐夫正在上体育课,他赶紧拉住小舅子,一起去体委打听。
周宁安以前就是体委的,后来“文革”砸烂体委,他才来到二中。这时候体委已经恢复工作了。来体委后,跟周宁安有过矛盾的李主任说根本没有接到任何通知,问急了,他才推说是县里的决定,说上山下乡不到一年的知青不准调动。周火了,“省里的调令也不行?你整我可以,你别把我小舅子的前途给耽误了!”他直接来到龙海县革委会找一位姓方的副主任(相当于副县长),工作人员说主任感冒去医院了。周宁安又跑到医院堵方主任,他把许夕通的一沓信件和电报拿了出来,“忠和是要去参加国际比赛呀,福建队就是代表国家呢。万一因为忠和没去,队伍在国外输球丢人,国家体委怪罪下来,谁来担这个责任?”方主任了解到是体委卡住了陈忠和的调令,拍板让陈忠和立刻去报到,周宁安长了个心眼,“主任你得给我个尚方宝剑,要不还有人卡。另外,体委必须派一个人跟我一起去农场接忠和!”
方主任立刻写了一个让农场放人的纸条。
到了农场,大姐夫拉着小舅子就走,“ 粮食关系和档案回头办, 先赶紧去福州!”两个人骑车回到石码时已经下午5点了。一家人又兴奋又伤感。妈妈姐姐千嘱咐万叮咛,爸爸把儿子的唯一一双球鞋塞进包裹里,他会针线,还仔细地把已经破了洞的包裹缝好。
那时从龙海去福州要到漳州坐汽车,早上5点出发,要到下午5点才能到(现在只要3个半小时)。即使马上出发,也只能赶第二天的车了,而且还得花钱住一晚招待所。周宁安想了个办法,“连夜走!汽车不行,不还有火车嘛!”正好有一班厦门到福州的火车,晚上9点路过龙海附近的郭坑站。周宁安跑出去找到在工商银行当行长的朋友,将全银行唯一的北京吉普借了去。
第二天5点多,背着行囊的陈忠和站到了省体工队的大门口。一直等到8点多,他才敲开了恩师许夕通的家门。在省队,陈忠和待了一年多。懂事的他赢得了体工队上上下下的好感。但那时福建队人才济济,条件一般的陈忠和也面临淘汰的窘境。省队也舍不得他走,让忠和回县里太委屈了,他们找了个机会,送他到北京考了一级裁判。陈忠和成了福建队的随队裁判,吹了一年多的比赛。
命运又一次青睐了他。1981年,袁伟民率领中国女排来漳州集训,对当时在福建工作的国家男排主教练戴廷斌说,他想找一个作风正派、技术比较全面、个子不太高的男队员来加强女排训练。戴当即说道:“我有一人,保证在女排不出事,也保你满意。”
|
编辑:
李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