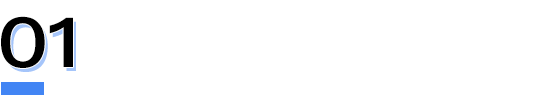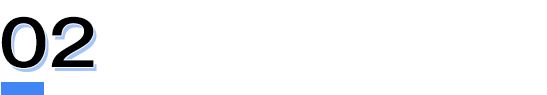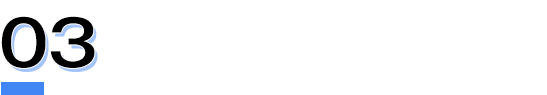在人间最绝望的角落里,足球闪着微光


独家抢先看
文 / 王帅
那个被世人称作「地带」的区域,破旧、拥挤、混乱,狭长得仿佛永远看不到尽头。
但对出生于此的汉娜·瓦埃勒·哈瓦杰莉(Hanan Wael Al-Hawajri)来说,那里有家和生活。
尽管日子艰苦,10来岁的她每天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父母给了她一双大长腿,而她不久前才加入一家名叫阿赫利·努塞拉特(Ahli Nuseirat)的足球俱乐部,那是整个地带的第三家、也是汉娜生活半径里唯一一家专为女孩设置的训练机构。教练说,他们打算组建一支女足,以后还可以去踢联赛。
汉娜想踢球,她想为家乡赢得冠军。
她训练刻苦、天赋突出,两条腿像小鹿一样迅捷灵活。她还会主动为球队招揽人才,把表妹和朋友拉进了队伍。
对她来说,艰难而平静的日常没什么不能承受的,她可以努力过好人生。
圈中为汉娜 图源:Palestine Chronicle
然后,空袭发生了。汉娜的家落下了炸弹。
「好在」,一切发生得足够快,没有太多痛苦。
死讯传回了俱乐部。女孩们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足球不只是一个游戏,它还蕴藏着生命的重量。
避难
「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我们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当加沙地带的人间惨剧通过互联网传到国内,或许每一个看到这些的国人,都会对上面这句话拥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难民营」这个概念对于我们当下的生活是陌生的,社会安定、供给富足的我们拥有足够的安全感。
但它并不代表,这个世界上没有「地狱」。
当死神可以无预警地随时降临,当基本的生存权成为一种奢侈,足球仿佛理应变成一种不切实际的谈资。
某种程度上,这是显而易见的。
加沙地带若干个大型体育场的断壁残垣,成了流离失所的难民们栖身的倚靠。荒芜的草坪上搭起了简易的帐篷,残破的球门被当作了晾晒衣物的架杆,跑道上废弃的替补席,更成为了男女老少聚在一起休憩饮食的「凉亭」。
与其说这里是体育场,不如说这里是避难所。
体育场成为百姓的避难所 图源:法新社
然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早就告诉人们,生存是第一性的,却从来不是唯一性的。当生存和安全需求得到满足后——哪怕只是暂时的,人们仍然会竭尽所能去追求更高层次的满足: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
——何必冒这样的风险?活着不好吗?
——但你有没有想过,对他们而言,活着和死去本就一样辛苦。
在加沙地带南部海边的汗尤尼斯城区(Khan Yunis),几十个孩子围坐在一块空闲的沙滩上,一位教练正在这片「临时足球场」给他们传授足球理论。
这是由巴勒斯坦足协官方支持的体教项目,在汗尤尼斯已经招募了80多个孩子。战争一开始,他们就失去了学校,只有这些随时随地能够开展的简易教育项目,算是一个让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发育不至于荒废的权宜之计。
联合国的有关部门也在尽可能提供帮助。相比于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流窜,聚在一起学点知识,总归是更安全的选择。
当然,这样的「安全」只不过聊胜于无。毕竟,空空荡荡、无遮无拦的场景中,一颗炮弹就足够摧毁一切。
但一周三次的足球课,成为了孩子们在艰难时日里的最大期盼。
大人们会给他们讲述这个「非正常国家」里足球英雄的故事,让这些在动乱中长大的儿童体会应有的社会交往,并且,「尽可能发掘其中的天才,希望有朝一日,他们会代表巴勒斯坦,站上国际足球的舞台。」
图源:巴勒斯坦足协
的确,足球无法果腹充饥、不能救死扶伤,但之于苦难中的人们,身处足球的时间,哪怕只有几十分钟,也足以帮助他们获得一种暂时「逃离现实」、对正常生活的「回归感」。
说白了,足球,也是他们精神的避难所。
所以哪怕是在最窘迫的处境中,足球都没有停止。
人们在沙滩踢球、在街角踢球、在遭到轰炸的废弃房屋旁清理出空地踢球。而这些永远不会被记录在案的比赛,每场都能自发聚集成百上千的现场观众,其中很多人还拄着拐、包着伤,掩盖着因战火而残缺的身体。
——生活里有这么多苦,要有多少甜才填得满啊?
——生活里有这么多苦,只要一丝甜就能填满。
当战局缓和,巴勒斯坦足协立即克服重重险阻,在海滩边组织了一场为期2天的小型锦标赛,让各家俱乐部里活下来的年轻人齐聚一堂。没有奖杯、没有队服、没有裁判、甚至没有比赛名,但赛后所有人在蓝天和阳光下与战争废墟的合影,却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因为那代表着:「我们仍在努力生活。」
图源:巴勒斯坦足协
「逃离现实」,在大多数语境里这都是一句带有贬义的评价,可对于死亡转瞬即至的难民,我们并没有资格对他们提出任何指点。逃离现实,对他们无异于一种幸福。
而在敌人看来,逃离现实,也意味着他们还没被打垮。
战争期间,以色列军队有计划地摧毁了加沙地带的50余个大中型公共体育设施,其中包括所有专业足球场,以及巴勒斯坦足协的总部。
他们甚至在攻占了亚尔穆克体育场后把这里改作了战俘营。
而这里,曾经是巴勒斯坦国家代表团为奥运会集训的地方。
创业
很多媒体都会把加沙形容为这个星球上最大的「露天监狱」,不过事实上,这个总面积360平方公里、分出了五大城区、生活着超过200万人的海岸地带,其体量已足够民间经济的产生。在没有硝烟的时间段里,那里也确实形成了一些基础的现代经济面貌。通过连接埃及的地道,加沙人偶尔还能吃到肯德基和麦当劳。
但在另一块「世界的边缘」,那里呈现的是另一种苦难,一种被所有人忘记的苦难。
在非洲肯尼亚和以海盗闻名的索马里边境区的不毛之地上,坐落着被联合国认定的全世界最大的难民营之一:达达阿布难民营(Dadaab Camp)。
1992年,为了接纳战争中的流民,联合国在这里用塑料布和木板搭起了简易的房屋。起初只是短暂的过渡之举,但索马里内战干戈不止,后来又接连遭遇了洪灾和干旱,得不到政府救援的底层百姓蜂拥而至,把希望寄托在了联合国身上。
就这样,在接下来的30年里,达达阿布逐渐演变成了包含四片营地、注册难民数最多超过38万的「无主之地」。
达达阿布难民营 图源:路透社
这里是肯尼亚的国土,但这里97%的人口是索马里人。两国羸弱不堪的政府根本不具备安置30万人口的治理能力。直到今天,如何处理这座难民营以及营地里的人,依旧是让联合国、肯尼亚和索马里头疼不已的难题。于是,他们被打上了一个自相矛盾的标记——「肯尼亚的索马里人」。
这是一群被世界「遗忘」的人。
周边的沙漠天然形成了「隔离带」,肯尼亚不想管、索马里管不了。离开难民营需要提前申请,但申请几乎不被批准。而如此严格的管理,恰恰是为了不用管理。
他们的生活被完全限制在其中。时至今日,这里的大部分公共设施都是靠着联合国向金主们四处化缘才勉强修建起来的。
而这里将近一半的人口只有不到18岁——他们从出生就从未离开。
极端的生存条件势必造成极端的心理状况。据统计,达达阿布的难民饱受抑郁、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疾病的困扰。青少年药物滥用、吸毒乃至自杀的比例更是高得吓人。
所幸,还有足球。
图源:半岛日报
我们无从查证是谁第一个组织比赛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没有战争威胁的地方,在30多万常驻人口的营地里划出几片球场、组织固定时间的联赛并不是什么难事。
球场越划越多(现在已经有上百个场地)、比赛安排也越来越规范。偶尔,索马里和肯尼亚的足球明星们还会来协助联合国,借助球赛向难民宣传公益知识。
每当四个营地的「冠军联赛」在黄昏时分打响,球场总会挤满上千名观众。这些比赛水平自然不算多高,球员们有的甚至还打着赤脚,但某种意义上,这才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球赛。
图源:大西洋月刊
但达达阿布最大的「足球明星」,是一个不踢足球的男人。
他叫奈伊塔(Nyieth),2013年因为南苏丹的内战颠沛至此。很快,他就感受到了难民营中物资的匮乏。偶然的机会,他被选中前往挪威接受小手工业的职业培训。回到难民营,他用几根木棍搭起了作坊。
问题来了:卖什么呢?
可能是一个商人本能的嗅觉,他发现达达阿布的球赛如火如荼,但「进口」足球一个要花30块钱。可足球,不就是把几块皮革缝在一起吗?
于是,「奈伊塔手作牌」的足球凭借仅需进口球一半的低价迅速抢占市场。起初,不熟练的奈伊塔3天才能缝好一个球,后来产能越来越高,至今,他一个人已经拿下了全营区30%的份额,连联合国的工作人员都来找他买足球。
奈伊塔和他的手工足球 图源:半岛日报
「如果能出入自由、订更多原材料,我还可以做更多。但现在没办法,我经常要等着从营区外寄进来的皮料。」
奈伊塔知道,足球是达达阿布的人们活下去的希望,也是他自己的希望。「我早就研究过了,这里的人们离不开体育,如果有可能,我想做一家做体育装备的企业。从难民营做起,做到外面去,我能成功的。」
所以在全世界最大的难民营里,足球值多少钱?
15块,或者,无价之宝。
发声
某位臭名昭著的前美国国务卿曾经在一次国际局势论坛上不加掩饰地声称:「对于国家而言,要么上桌点菜,要么成为菜谱。」
傲慢、尖刻、残忍,但某种意义上,却是真相。
不是所有国家都拥有平等的存在感和话语权。对于绝大部分小国而言,让世界看到和听到自己,本身就是一种极其稀有的「资源」。
这也是小国们往往重视体育的原因——体育的场景提供了国际舞台上一个平等的例外。
2016年,当苏格兰凯尔特人队的激进左翼球迷团体「绿色卫队(Green Brigade)」,在对阵以色列贝尔谢巴工人队的欧冠比赛中亮出几十面巴勒斯坦国旗,对那里的人民而言,那是靠他们自己根本无力完成的「呼喊」。
图源:SNS
出于「不允许在球场进行政治表达」的规定,欧足联对凯尔特人队执行了8600镑的罚款。「绿色卫队」顺势发起筹款活动,最终的募集金额超过了17万镑。在交完罚款后,剩余资金被捐赠给了约旦河西岸最著名、最古老的艾达难民营(Aida Camp)。
看到足球所引发的巨大舆论声量,难民营里的人们决定有样学样。为了表达对「绿色卫队」的感谢之情,这支球队被命名为「拉吉凯尔特人(Lajee Celtic)」。Lajee,就是阿拉伯语「难民」的意思。
他们知道FIFA的规矩,所以干脆把自己的球衣设计成了巴勒斯坦国旗的样子——为了规避处罚,他们又在国旗那块红色的三角形区域里,画上了一个代表太阳的笑脸。
把国旗穿在身上的拉吉凯尔特人象征着什么,所有人心知肚明。
图源:Lajee Celtic
2016年就已组队的他们,至今仍然无法注册为职业俱乐部。和前面的故事一样,他们只得通过各种不被记录的友谊赛和民间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
并且,出于对包括「绿色卫队」在内的支持者的保护,在球队的社交媒体上,所有合影的人脸都被打上了马赛克。
就是这样一支连「户口」都没有的球队,却得到了巨大的认可。他们被邀请去非洲巡回比赛、去摇滚音乐节当嘉宾,他们的球衣变成了文化icon,官网永远显示断货。连坎通纳都穿上他们的球衣拍照,以此亮明自己的态度。
「打仗的事我们无能为力,但只要这支球队还在,同胞们就会知道,始终有人在为巴勒斯坦的挣扎发声。」
图源:坎通纳个人社媒
当地时间1月15日晚,以色列和哈马斯终于在各方的不懈努力下达成了停火。尽管大家都知道,在中东,停火协议有多「薄」——它能否实现,往往只取决于强的那一方是否愿意停下。
而最新的消息是,刚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表示,打算「接管」加沙地带,并把这里的人民「安置」到其它国家。
也就是说,坚持了这么久,那里的人们却可能连一个称之为「家」的地方都留不住。
诚然,在漫长而艰难的生存之战中,体育什么都改变不了,却是当下他们唯一能找到的快乐。
毕竟,这里是全世界最接近「地狱」的地方。
这里没有新闻。
“特别声明:以上作品内容(包括在内的视频、图片或音频)为凤凰网旗下自媒体平台“大风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videos, pictures and audi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the user of Dafeng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mere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pac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