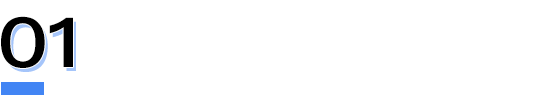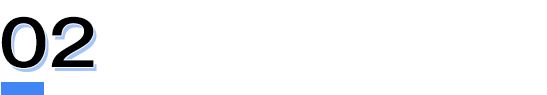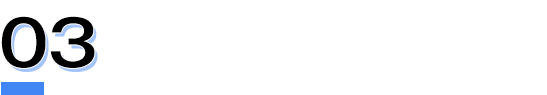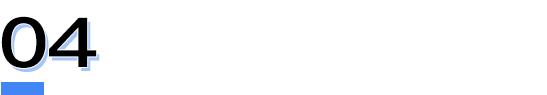一条河隔出两个体育帝国:达斯勒家族的荣耀、背叛与孤独


独家抢先看
生命中曾经有过的所有喧嚣,都将用寂寞来偿还。
▂
文 / 莫空
前不久,彪马宣布任命Arthur Hoeld出任品牌新CEO,将于7月1日正式上任。而在这份突然的官宣之外,最为大众津津乐道的便是Hoeld的身份——阿迪达斯前董事会成员。
彪马想要复刻阿迪的翻盘?其实,这两家运动品牌「共享」高管,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带领阿迪打出翻身仗的现任CEO比约恩·古尔登(Bjørn Gulden),之前的身份正是彪马的CEO。
如此频繁的高管跨阵营流动背后,是这两家德国品牌从诞生之初便刻入基因的「血缘羁绊」。
达斯勒兄弟,鞋厂起家
我们先来认识一个名字——克里斯托夫·达斯勒。
作为一名在巴伐利亚州纽伦堡以北几英里的赫尔佐根奥拉赫小镇出生的人,他的家族沿袭着镇子的传统,从中世纪开始就世代以纺织厂染布料为生。
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席卷德国,让达斯勒的家族无法再以此为生。作为家族纺织厂最后一代,克里斯托夫选择离开。
和所有在外省漂泊打拼的年轻人一样,克里斯托夫·达斯勒因为要安家,最终又回到了故土。他的两个儿子鲁道夫·达斯勒和阿道夫·达斯勒,便是在老家赫尔佐根奥拉赫出生的。
那时候,小镇上的支柱产业已经从原来的纺织加工,变成了重型毛毡拖鞋。为了生计,克里斯托夫在鞋厂找了份工作,而他的妻子则开了一个小型洗衣房。
两个日后大型体育用品品牌的创始人,便是在如此艰难,充斥着衣服与鞋子的环境下成长起来。
达斯勒兄弟
20世纪初,德国主流认可的运动不是足球,而是体操。甚至一些保守的德国早期现代体育从事者认为,足球是一项鲁莽野蛮有辱人格的运动。所以在阿道夫·达斯勒的童年,他的主要运动方式并非足球,而是野外长跑,到了冬天又变成滑雪。
但快乐自由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一战的打响毁掉了一切。
阿道夫的两个哥哥,大哥弗里茨·达斯勒和二哥鲁道夫·达斯勒都被征兵进了军队,四年时间全部陷在佛兰德斯泥泞的堑壕战里。
阿道夫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他作为学生、家中剩下的独子,没有被立即征召前线。然而,到了一战后期,年仅17岁的他还是被招往了比利时边境,1918年,与两位哥哥在战争前线汇合。
幸运的是,达斯勒一家三个男孩大难不死,全都安全回到了赫佐根奥拉赫。
阿道夫·达斯勒是三兄弟中最先觉醒创业头脑的。在父母和兄长的支持下,他通过捡战后废品,把母亲的洗衣房变成了自己的小型制鞋作坊。不仅如此,阿道夫还非常擅长动手改装,就像他夫人凯瑟·达斯勒所说,「制鞋不仅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爱好。」
由于对长跑的了解,很快他便在铁匠朋友弗里茨·泽莱因的帮助下,制作了一批早期的带钉运动鞋。
曾经在制鞋工厂正经学过手艺的二哥鲁道夫,看到弟弟阿道夫的制鞋作坊搞得颇有些眉目,决定加入这个家族制鞋作坊——阿道夫主管生产,鲁道夫则主管销售,达斯勒兄弟的鞋厂便从这里起家了。
一战后的德国日子并不好过。
但与战前不同的是,没有了德皇保守派的约束,现代体育在德国野蛮生长起来,曾经不被允许的拳击俱乐部、足球俱乐部也遍地开花。喜欢运动的阿道夫也加入了当地俱乐部,担任过前锋——也正是如此,阿道夫看到了运动品牌的商机。
比赛时,大批球迷挤满年久失修的体育场。阿道夫意识到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要来了。
与战争更近
1927年,达斯勒兄弟得到的第一笔大订单正是来自赫尔佐根奥拉赫体育俱乐部。为了满足这个订单,他们搬到了赫尔佐根奥拉赫一家荒废的小工厂,并雇佣了20多名工人,扩大生产。
有了从零到一的突破,达斯勒兄弟的鞋厂也逐渐得到了业内人士的赏识。
首先表现出兴趣的是德国前奥运会选手、担任德国奥运会田径队教练的约瑟夫·韦茨。他专程从慕尼黑来到镇上考察,从改进鞋类聊到提高运动成绩,双方很快成了朋友。
有了来自国家队的渠道,达斯勒跑鞋的营销渠道也是越来越广,从足球、田径发展到了拳击等项目,从鞋子发展到拳击袋、背包、t恤等不同的装备,达斯勒鞋厂已经不仅仅是在赫尔佐根奥拉赫走红,而是逐渐走向德国,甚至通过奥运会走向全世界。
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达斯勒兄弟为德国中长跑运动员莉娜·拉德克(Lina Radke)制作了专属跑鞋
而达斯勒兄弟走向世界的标志性事件,是赞助了美国运动员杰西·欧文斯。
在1936年那一届「政治大棒旗下」的柏林奥运会,达斯勒兄弟不仅提供了德国国家队的赞助,还赞助了一个非德国国籍,非宣传中的「纯种雅利安人」,并让他一举夺得两枚金牌,并击败了德国田径接力队。
达斯勒兄弟在声名大噪的同时,也逐渐成了德国纳粹眼中可利用的人才。
杰西·欧文斯
早在赞助欧文斯之前,鲁道夫就已经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投上了自己的选票,这是达斯勒家族第一个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投票的。这个党后来的领袖,是另一位著名的「阿道夫」。
纳粹以惊人的势头迅速席卷德国政坛后,达斯勒一家三兄弟弗里茨、鲁道夫、阿道夫都加入了纳粹党。
与更为激进参与政治的二哥鲁道夫不同,阿道夫加入纳粹党的理由更像是一个产品经理的做法。他觉得,纳粹党如此倡导体育运动在国家中的形象,那么这个党派选择对今后体育运动上的订单一定会有帮助。
并且,在加入纳粹党后,阿道夫并没有走政治路线。按照之前的分配,他依然把厂里的营销宣传任务交给鲁道夫,大哥弗里茨则去开发非球鞋品类的业务,而他自己却去了德法边境拜师学习更先进的皮革制造技术。
柏林奥运会的浪潮后,达斯勒鞋厂每年的销售额已经达到约20万双。但此时,销量、品牌、影响力,在即将到来的战争面前一文不值。
1939年8月28日,希特勒规定了所有必需品采用配给制度,包括鞋类。作为纳粹党经济改革的一部分,当时德国的鞋类生产由德国皮革工业集团负责监督,虽然皮革对战争的重要性并不像钢铁和燃料那样是绝对刚需,但因为能造出国防军制造靴子、手套和其他军用装备,所以达斯勒兄弟的工厂依然被认为具有战略重要性。
但这也让达斯勒一家,离战争更近了。
阿迪达斯和彪马,兄弟分家
1940年8月,阿道夫收到国防军的信件:12月初,他将奉命在纽伦堡附近的布亨布尔镇第13情报团接受无线电技术员培训。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在军队里干多久,在服役不到三个月后,就又回到了老家的鞋厂里。
战争初期,纳粹为了笼络人心,还让达斯勒鞋厂的配额从每年6000双提高到了10000双,并允许他们少量销往国外,这在当时的德国企业中绝对是特殊的。
然而达斯勒一家的分裂,也是从此开始的。
最先分家的是大哥弗里茨·达斯勒。当时他已经不管鞋厂业务,而是经营达斯勒分厂的短裤t恤工厂,在战争期间被征用来为德国士兵生产皮包。本身经营已经不在一起,政见不同更是让二人彻底各奔东西。
而与二哥鲁道夫的分家,就更为复杂。
战争后期1943年1月,阿道夫因为鞋厂里技术骨干的身份再次逃离了被征兵的命运,但鲁道夫却被征召到了萨克森前线。在一次休假时,他重回家乡工厂,向还留在厂里的工人讲述他的规划时,工人们对他置若罔闻。
此后,阿道夫的鞋厂彻底沦为了纳粹军工零件生产基地。但鲁道夫人在境外,还在通过各方人脉施压,要求达斯勒鞋厂生产拥有鲁道夫个人专利的跳伞靴设备,以求重新掌控公司话语权。
此时,鲁道夫和阿道夫兄弟之间已经产生了间隙。
1945年4月4日,老父亲克里斯托夫下葬。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老达斯勒,死于心力衰竭,达斯勒一家在赫尔佐根奥拉赫短暂重聚。
葬礼结束的第二天,鲁道夫就被盖世太保带走了,短暂从集中营被解救不到几天后,又被美国人抓了起来——鲁道夫坚信,两次被抓,是因为阿道夫的告密。
但实际上,阿道夫彼时正在处理达斯勒鞋厂战后混乱的危机。
阿道夫·达斯勒鞋厂由于技术优势,成为了美国陆军认为有价值的厂牌。在允许鞋厂继续开工为美军生产的同时,后者还提出暂时征收阿道夫一家的住所,迫使他们一家人不得不搬到塔楼里。
1946年7月31日,鲁道夫被释放回家。然而他当时的处境已经面目全非,在工厂中更是完全失去了话语权。
猜忌和矛盾让两兄弟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大战,最终走向了分家的结果。
鲁道夫把财产做了最后清点,阿道夫同意哥哥接管维尔茨堡大街的一家小鞋厂,而他本人继续带着家人住在塔楼内,并管理火车站附近的大工厂。
厂里的销售团队和技术团队也参与了这次分家,大多数销售团队跟着鲁道夫去到维尔茨堡大街,技术人员则几乎都选择留在了阿道夫身边。
1948年4月,两兄弟分家事宜全部完成。阿道夫很快申请注册一家名为「Addas」的公司,由于太过类似德国另一家童鞋厂被拒绝,微调之后,风靡世界的阿迪达斯诞生了。
另一边,鲁道夫也使用「Ruda」注册公司,同样被驳回,理由是太粗俗,鲁道夫便把注册名改为了「Puma」。
赫佐根奥拉赫小镇以奥拉赫河左右岸,成了两家兄弟、两个公司传奇的分界线。
一场战争,兄弟隔墙,一个厂变身两个厂。成了同行死敌,兄弟纷争依然不在少数,并且战火一直烧到了两家公司下一代继承人手上。
达斯勒家族史后,阿迪达斯与彪马的商战史随即开启。
「鸡娃」战争与父子相斗
霍斯特·达斯勒,是阿道夫和妻子凯特·达斯勒的长子,也是阿道夫家唯一的男孩,阿迪达斯的接班人。
电视转播让1956年奥运会开始进入新的时代。彼时年仅二十岁的霍斯特希望去闯一闯,想要把阿迪达斯这个品牌推广到墨尔本奥运会上——整个阿迪达斯公司当时只有他一个人勉强能说英语,自然这个重任都落在了他的身上。
霍斯特·达斯勒
自从达斯勒兄弟分家后,整个家族连带着他们所在的小城也变得硝烟四起。小镇以奥拉赫河为界的左右岸,像霍斯特这样的孩子是不允许与河对岸叔叔家的孩子们玩耍的,尽管他们是十分亲密的堂兄弟。
父辈们的战争沿袭到儿子辈,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鸡娃」,各自都要把自己的儿子们培养成优秀的接班人。
在很小的时候,霍斯特就被父亲拉着去森林里长跑,一跑就是几个小时。毕竟,作为阿迪达斯的接班人,不仅要亲自了解一项运动,也要有一个工作狂的好身体。
霍斯特多年后回忆道,他和他父亲的相处模式也是不正常的,更像是父子之间的比赛,霍斯特对父亲只有尊重和钦佩,但不会有任何亲密的感情。
同时,鲁道夫家的两个儿子与父亲也不算和睦。
鲁道夫的大儿子阿明·达斯勒本就对继承家业没有兴趣,他更感兴趣的是那时候刚兴起的电子工业,但作为家中长子,彪马的大任依然是压在他头上的大山。
阿明·达斯勒
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霍斯特已经敏锐感觉到了电视时代带来的全球新商机。
本来按原计划,霍斯特的主要工作是向住在奥运村的运动员推广阿迪鞋子,属于传统销售模式。但当他见过了阿迪达斯在墨尔本的诸多经销商和分销商后,开始有了一个大胆且疯狂的计划——向奥运村的运动员们「赠送」阿迪达斯的鞋子。
那时候,奥运会或世界大赛的「业余主义」导向盛行,即便当时已经出现了运动品牌赞助某只球队或者某位球员的装备,也不能明目张胆表露出具体品牌。
所以在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霍斯特想要让运动员们穿上阿迪达斯的鞋子、装备,在刚兴起的电视转播面前为大众做免费广告,是一件极其困难且非常要开拓精神的事情。
另外,在还掌握着阿迪达斯实权的阿道夫看来,儿子如此大批想搞赠送球鞋的想法,实在是有些激进和异想天开。但霍斯特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和三寸不烂之舌,真的为家族闯出了新机遇:
德里克·伊博森,这位世界上首个在4分钟内跑完一英里的英国运动员,就从墨尔本奥运会开始穿上了阿迪达斯的鞋子,并且之后回到英国,也一直穿着它;美国运动员阿尔·欧特,由于他在整个美国都没有找到合适自己大小尺寸的鞋子,还是阿迪达斯为他解了燃眉之急,他也很争气的在墨尔本奥运会上赢得了3枚金牌,成了阿迪达斯忠实用户……
凭借霍斯特的大胆创意,还有墨尔本经销商们的努力,那届奥运会已经有超过70%的运动员被阿迪达斯征服。
对于能够免费获得阿迪达斯装备,运动员们都觉得是个很大的福利,也自然而然成了前者的免费广告。而当他们手拿金牌出现在各大知名杂志头版头条上时,阿迪达斯的销量也水涨船高。
墨尔本奥运会使霍斯特一战成名,「一个免费提供球鞋的男孩」成了他的标签,而这个标签日后成了他在国际体育圈叱咤风云的关键。
再看阿迪达斯的对家——彪马,却陷入了父子内斗的泥沼。
阿明达斯勒其实一直有关注堂弟霍斯特的动向。在他看来,彪马要拿到更多的订单,超过阿迪达斯,就必须要给运动员更多福利,包括但不限于送鞋子、装备等,却遭到了父亲鲁道夫的坚决反对。
甚至在阿明于奥地利当地要收购一家体育用品工厂时,固执的父亲拒绝向奥地利银行提供任何担保资金,理由是阿明不是在推销球鞋,而是在生产滑雪用品。
然而实际上,坐在德国的鲁道夫没有想到,在奥地利体育市场就是有一定的应季性的——进入下半年,奥地利人大部分周末时间的运动就变成了在滑雪,此时再推销任何运动鞋都是毫无意义的。
阿明也没有放弃。没有了父亲的帮助,他依靠在美国经销商的关系,开始出产「达斯勒」球鞋——实际上这款球鞋依然是用的彪马的产品线,却也算是阿明向父亲发出的挑战。
不过,美国的经销商们乐于帮助阿明销售他的「达斯勒球鞋」。这样一来,阿明就有了足够的现金流,继续他在奥地利体育用品市场的开拓创新。
而这次和父亲的内斗,直接导致了父亲完全在一段时间断绝了和阿明的关系。由于父子内斗,在霍斯特已经在阿迪达斯大展拳脚的时候,彪马还停留在原地,也没有赶上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的新市场红利。
终于在彪马掌握了实权的阿明也开始了向运动员赞助的策略。而他锁定的第一个赞助目标人物,就导致了阿迪达斯和彪马的「短兵相接」。
短兵相接
阿明·哈里是德国的短跑运动员。年轻时他曾练足球,直到16岁才专项练习短跑,天赋强大的他转赛道仅仅几年后,在1958年欧洲锦标赛上就获得了100米和4×100米的冠军。
作为德国本土选手,他自然也成为了阿迪达斯和彪马争夺的对象,两家公司都希望宣传「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穿的是自家的鞋子。
本来在这个赛道上,阿迪达斯是遥遥领先的,阿明·哈里与霍斯特的关系更为密切。而在一次家宴上,阿明·哈里提出条件:阿迪达斯对其直接提供金钱赞助,或让他成为日后在美国的独家经销商。
阿迪达斯不愿开这个先例,拒绝了他。
阿明·哈里被彪马盯上了。前者穿着彪马的鞋子在欧洲锦标赛和1960年罗马奥运会上大出风头,这场阿迪达斯和彪马的第一次赞助运动员之战,以后者的胜利告终。
而这次的短兵相接,也让阿迪达斯创始人阿道夫和彪马创始人鲁道夫彻底意识到,家族竞争的接力棒应该正式交到儿子们手里,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了。
阿明·哈里
如果说奥运会开启了儿子们的战争,那么1966年和1970年两届世界杯,就是阿迪达斯和彪马「儿子们」全面开战的巅峰。
那时候,电视转播逐渐成为足球世界里司空见惯的事,虽然各大协会组织、赛会组织还并不允许明目张胆让赞助商直接送钱给运动员,但实际上,阿迪达斯和彪马早就开始各种暗地里用钱和协议换取运动员的品牌使用权,也就是现在人们熟知的品牌代言人套路。
阿迪达斯进入足球圈,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在伯尔尼奇迹那年,德国队用的就是阿迪达斯的装备,霍斯特在打入法国市场的时候重用的方丹,也是法国足球的代表人物,曾在一届世界杯上打进13球,退役后成了阿迪达斯在法国的商业代表。
而且,方丹的确向霍斯特提出了有效的建议,希望阿迪达斯能生产属于自己品牌且非常有记忆点外观的足球。于是,阿迪达斯的黑白橡胶相间的足球就从德国走向法国,并走向了整个欧洲大陆。
方丹
德法的足球市场已经让阿迪达斯拿下了很多订单,但他们又是如何挤进英伦三岛呢?
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英国人非常迷信的民族品牌(比如Villain维纶)都不太关心鞋的款式和舒适度,这给一些盘带为主的技术性球员造成了不小的困扰;另一方面,当时英伦更为著名的体育用品品牌茵宝还没有开始进军球鞋市场,这也给了阿迪达斯可乘之机。
更好的产品意味着更大的市场——当阿迪达斯从1961年开始在英伦三岛正式铺货销售时,英国球员一夜之间穿厚靴子的习惯突然间消失了。而茵宝直到此时也没有急于抢占球鞋市场份额,反而在自家门店允许阿迪达斯出售他们的球鞋。
当时的茵宝在足球市场是个大品牌。1966年世界杯前夕,世界杯决赛阶段的16支球队中,有15支都与茵宝签了球衣合同。阿迪达斯凭借与茵宝的战略合作关系,让这些球队也几乎都签订了他们的球鞋合同。
不过,这些赛会工作人员(比如球童、裁判等)的制服装备提供也是一笔重要的订单,除了阿迪达斯和茵宝,英国另一家传统品牌Bukta,和彪马也都在暗暗竞争着这笔订单。
而阿迪达斯凭借与英格兰队长鲍比·摩尔的良好关系,以及茵宝与英足总秘书阿尔夫·拉姆齐的良好关系,最终不仅让1966年世界杯开幕式上所有的工作人员统一穿上了自家球鞋,而且还拿下了英格兰国家队的球鞋装备订单。
球队赞助市场饱和,彪马便改变赛道,以影响力取胜。比如,著名的「黑豹」尤西比奥,当时就被阿明撬去了彪马,这的确吸引走了不少人的目光,毕竟比起裁判和球童,大多数人更关注的是注意球星脚下的球鞋。
尤西比奥
然而打进1966年世界杯决赛圈的,是英格兰和德国。
由于当时大家都很难想象德国球员会穿着阿迪以外的品牌上场,当时彪马唯一的希望,就是说服一些英国球员将球鞋临时换成彪马,金钱诱惑成了主要手段。
可阿迪达斯同样舍得下重金,于是就在临决赛开赛之前,双方开始在英格兰球员之间展开了一场金钱拉锯战。直到当年轻的英格兰国脚阿兰·鲍尔在离决赛开始的两小时前,拿着阿迪达斯给他的特约赞助费两千英镑在酒店狂撒的时候,大家才意识到这不对劲。
最终当决赛哨声吹响的时候,人们惊奇的发现还真有几个球员没穿阿迪达斯的球鞋,比如雷·威尔逊、戈登·班克斯,尤其是出镜率是相当高的英格兰门神班克斯穿着一双彪马足球鞋,也让后者终于尝到了一点世界杯决赛的甜头。
短暂的和平,与更多的矛盾
阿迪达斯和彪马的商业撕扯大战,已经引来了太多政治关注的目光,尤其还害得阿明·达斯勒无辜坐了几天牢,这让达斯勒家族在生命面前还是暂且放下了矛盾。
最终,在当时墨西哥政治局势非常微妙的情况下,一家人团结一致,把阿明平安地接回了德国。
1970年世界杯,即便双方都很清楚贝利的代言是巨大的「蛋糕」,但为了暂时的和平,不展开无休止的价格战,即便是阿迪拿下了巴西国家队球鞋赞助,也没有为贝利提供一双阿迪鞋。
然而,彪马最终还是打破了这项「贝利协议」。
淘汰赛开赛前一天,彪马拿出了对贝利价值两万五千美元的合约,让他在墨西哥世界杯上穿彪马鞋子,并且在未来的四年内分期付款十万美元,让贝利正式成为彪马的代言人。
于是就出现了贝利在开赛前一分钟蹲下慢慢系鞋带,特写镜头扫过,全世界数百万台电视机看到贝利穿彪马球鞋的名场面。那一次,贝利成了巴西队绝对的国王,彪马的曝光率也来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贝利穿着彪马的装备
而这桩和贝利的交易证实了,阿明以及彪马后来对抗阿迪达斯的主要策略——阿迪达斯的目标是让每个不同技能水平的球员都穿上阿迪达斯的鞋子,而阿明则认为彪马就专注少数更有魅力和国际水平的球员。也就是阿迪抢数量,彪马就抢流量。
这样的公司策略也影响到后来彪马签人的策略,比如和克鲁伊夫著名的代言合同,也是按照这个运营思路来的。
当时荷兰队的球衣赞助商是阿迪达斯,而克鲁伊夫与彪马的协议,自然会产生纠纷。在彪马的另一个执掌人格尔德·达斯勒几乎和霍斯特又闹翻的情况下,以及在各方利益的拉扯下,最终同意克鲁伊夫可以从他的球衣上去掉一条条纹,球鞋也可以继续穿彪马。
这自然让彪马很高兴,他们在继续执行荷兰队头号球星赞助和广告效应时,还能编出更丰富的人设和故事,即「反叛品牌和反叛玩家找到了他们的精神,并一起合作」,更增强了品牌产品之外的文化效应。
克鲁伊夫在比赛中身穿特制的球衣
但很有意思的是,这位欧洲巨星实际上更喜欢穿阿迪达斯的鞋子。甚至有一次在训练中,克鲁伊夫无意露出了自己的阿迪球鞋,这差点让彪马终止与这位荷兰飞人的高额合同。
不过那次的世界杯依然是阿迪达斯与德国人大获全胜,因为又是贝肯鲍尔领衔的德国队拿下了世界杯冠军。
1974年也的确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不仅是因为经此世界杯一战,阿迪达斯和彪马的市场争夺战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更因为这一年下半年,彪马的一代创始人鲁道夫·达斯勒,因肺癌生命画上了句号。
而他留下的彪马公司的分配,以及巨额的遗产,则因为他自己的任性和偏心,最终险些酿成彪马两兄弟阿明·达斯勒和格尔德·达斯勒的兄弟内战。
内耗往往是一家公司最忌讳的。而使彪马更加危机四伏的,不仅是霍斯特执掌下最终通过政治高层上升通道,坐稳了体育品牌老大位置的阿迪达斯,还有已经起势的另一运动品牌——耐克。
旧时代的残党
1974年鲁道夫·达斯勒在死之前几个月,都在翻来覆去地修改遗嘱,也正是这翻来覆去的改变,让彪马的两兄弟阿明和格尔德有所间隙。
而同样震荡的还有赫佐根奥拉赫河的另一岸,在鲁道夫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里,一个友善的的牧师想撮合阿迪达斯的一代创始人阿道夫·达斯勒,与他的兄弟最后和解。
其实在墨西哥奥运会后,两兄弟也并不是河两岸从没有见过,在纽伦堡大酒店,在法兰克福机场实际上他们都为公司和业务的事长时间讨论过。
但业务是业务,家事是家事,阿迪达斯一代目和彪马一代目并没有以家人的身份见面,甚至为业务讨论的事连他们的家人都不知道,这还是许多年后阿道夫的助手接受采访时才说出来的。
不过在鲁道夫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里,阿道夫拒绝了牧师的请求,最终没有以家人的身份兄弟之间达成和解。
甚至鲁道夫去世后,阿迪达斯发表的声明也是十分傲慢:「很遗憾,阿道夫·达斯勒的家人不会对鲁道夫·达斯勒的死发表任何评论,凯瑟琳·达斯勒和阿道夫的长女英格·本特将作为代表参加葬礼。」
阿迪达斯和彪马的一代早早给这两个品牌定下了基调。
鲁道夫是当时两兄弟创业之初掌管营销的,而阿道夫是掌管球鞋技术的,一直到两兄弟各自离世的头几年里,鲁道夫依然热衷于在家里开派对结交各路名流,而阿道夫则更像一个技术工匠。
阿道夫在病床上养病时对他的私人医生说,他并不知道阿迪达斯现在在全球开了多少家工厂。但从业五十多年来,他以自己的名义注册了近700项专利。
阿道夫·达斯勒
1976年,阿道夫去世的两年前,他依然观看着奥运会田径比赛,甚至在古巴著名田径运动员胡安托雷纳比赛时,告诉他的助手维特曼赶紧去和这个来自古巴的运动员谈谈,他的鞋子在预赛中出现了问题。
通过阿迪达斯当面的矫正之后,胡安托雷纳的确在后来的400米和800米比赛中都拿到了金牌。
后来,越来越多人都想在赫尔佐根奥拉赫小镇一睹阿道夫·达斯勒的真容。有一次,他正在小镇遛狗,有人在门口叫他,可阿道夫却耸耸肩说,「我不知道,我只是园丁」,那时候阿道夫就穿了一件十分普通的外套和阿迪达斯牛仔裤。
但这个园丁,硬是用自己的七百多项专利一点点把阿迪达斯浇灌成一个国际巨头。
就在鲁道夫离世的四年后,1978年9月6日,阿道夫·达斯勒的生命也走到了终点。两天后一个简单的私人葬礼之后,阿道夫被埋在了赫尔佐根奥拉赫公墓,离四年前他哥哥鲁道夫的墓碑尽可能远的地方。
但时代已经不属于他们了。
向上发展
尽管上一代人都离去了,但影响力却并没有马上消退。
作为阿道夫的儿子,霍斯特虽然知道产品的重要性,但善于社交的他更觉得,下一个世代的体育用品产品,更是应该抓住电视传媒这个风口,同时也要抓住政坛风云变化的风口。
这使得他与他的母亲凯瑟·达斯勒,在阿迪达斯很多战略规划上有了明显的分歧。
霍斯特的生意经里有这么一句话,「一切的生意经都是建立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上的」。他也的确是这么践行实践的。
在德法边境的阿尔萨斯,兰德斯海姆镇科赫斯伯格旅馆早就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阿迪达斯度假山庄,那是霍斯特在这里买下的山庄旅馆,这里有米其林两星主厨,有阿尔萨斯最著名的酒窖,私人飞机也能在整个庄园进进出出,这里不仅作为阿迪达斯每年高层「团建」所用,只要阿迪达斯需要商谈重要的大事,霍斯特都会让贵宾在这里住上一阵。
比如当年和阿迪达斯第一个签约的篮球明星天勾贾巴尔,每次来兰德斯海姆,度假酒店就要为他单独加床,只因为2.18米高的巨人已经是当时来这的明星中最高的一位了。
再后来这里就不仅仅是接待体育明星了,还有很多政界商界的名流。
萨马兰奇(左三)造访科赫斯伯格旅馆
阿迪达斯这样的模式对东德也有效。东德国家元首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就曾亲自与阿迪达斯签署了一项协议,尽管东德不能从西德进口任何消费品,但作为国家资源,培养运动员、为运动员提供「国家派发」性质的运动装备、为运动员提供运动医疗,依然是阿迪达斯打入东德市场的绝好机会。
而河对岸的彪马提出过一系列比阿迪达斯更昂贵的赞助方案,依然被东德数次拒绝。
阿迪达斯对足球市场的重视自然是从阿道夫·达斯勒就开始的,但真正让阿迪达斯通过高层政治关系走进大赛,甚至进行大赛垄断,还是在霍斯特执掌时期。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阿迪达斯进军英格兰市场的时候,就与他们的英国朋友斯坦利·罗斯(Stanley Rous)打过交道,就是后来一路从欧足联主席当到国际足联主席的英国人。
1974年国际足联换届选举的时候,霍斯特当然还是鼎力支持他们的老朋友斯坦利。但是由于在对待非洲尤其是南非种族隔离制足球上,「欧洲中心论」的斯坦利依然支持种族隔离制度,使得他最终在选票上输给了来自巴西,非常懂得用「第三世界」足球发展论来赢得选票的阿维兰热。
阿维兰热治下的FIFA和霍斯特主导的阿迪达斯,最终组成了一家专门为FIFA和阿迪达斯营销服务的ISL以及它的母公司,而早在1974年国际足联换届完毕的这一年,霍斯特就与阿维兰热达成了共识。
这种共识就包括霍斯特和阿维兰热对非洲市场的一致看好,最省流的总结就是,霍斯特需要在非洲这个蓝海市场卖阿迪达斯,而阿维兰热则需要非洲国家在接下来的选举任命和世界杯主办权大票仓,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1970年世界杯上与霍斯特私交甚笃的摩洛哥教练,南斯拉夫人维迪尼奇,就让他执教的摩洛哥全队都穿着阿迪达斯的球鞋亮相。到了1974年世界杯、1978年世界杯非洲区预选赛上,大多数非洲球队用的装备都成了阿迪达斯,而最终1974年在全世界人们面前亮相的非洲球队扎伊尔,以及1978年亮相的突尼斯,都是用的全套阿迪达斯品牌。
我们至今都很难知道阿迪达斯到底给非洲捐赠赞助了多少装备,但极为有意思也颇为讽刺的是,在当年托马斯·桑卡拉所住的地方,地下室里竟然发现了三千个阿迪达斯的用球。
这也足以佐证自阿维兰热上任以来,霍斯特凭借着这层关系,向非洲市场做了多少开拓性的市场工作。
就像如今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所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如果不是FIFA的赞助,很可能是发展不了足球的。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阿迪达斯为市场、FIFA为权力开拓非洲的举动,的确帮助一些非洲新兴国家发展体育运动,但紧接着而来的就是市场金钱的诱惑,权力的诱惑,让腐败黑暗的魔爪已经牢牢抓住了足球这项世界性运动。
河的两岸,只是先后崩盘
经历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与阿迪达斯疯狂对飚签约巨星之后,当阿迪达斯走上另外一条赛道时,阿明·达斯勒和他的彪马依然在延续做产品——找巨星签约赞助——卖广告——销售这样的单一模式。
这种单一模式,高价的签约,其实是非常有风险的,简单说来就是怕签约的巨星「塌房」。
彪马就在1986年摊上一个「塌房」的网球明星鲍里斯·贝克尔(Boris Becker)。阿明在贝克尔第二次赢得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后与贝克尔签订了一份超大的合同,然而他们显然压错了宝,最终的销售额并没有达到他们预估的水准,但超高的佣金已经要拖垮彪马。
以至于1987年1月,阿明和格尔德只能决定通过次级贷款,向公司注入6200万德国马克,来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
给已经被银行、合同、股东们搞得焦头烂额的阿明最重的一击的,还是来自于骨肉血脉相连的自家亲兄弟。
1987年3月,离霍斯特·达斯勒去世只剩下几周的时间,但霍斯特还是在布达佩斯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本来这场新闻发布会是公布在匈牙利首都开设全新阿迪达斯专卖店的情况,然而在发言时,霍斯特还是对阿明和彪马开始了评头论足,他认为彪马完全可以开始寻找新的买家,阿明·达斯勒正在制造一场可怕的银行丑闻。
此举完全击中了彪马的弱点。之后,越来越多的彪马持股人抛售彪马,与彪马深度合作的德意志银行,也正决定终止对彪马的贷款。
1987年10月19日,也就是霍斯特去世半年后,在慕尼黑喜来登酒店,彪马终于召开了延迟已久的股东大会,阿明最终被免职,接下来的几周内离开公司,而他的两个儿子,也被告知「不能因为他们是阿明·达斯勒的儿子就能继续在彪马白领薪水」。
在生意的失败,堂兄弟隔空雪上加霜的打击之下,阿明染上了疟疾,虽然好不容易从鬼门关中逃脱出来,但据他的儿子约尔格·达斯勒多年后接受采访时说,那时的父亲仿佛失去了求生意志,整天除了靠在床上,就是陷在沙发里,完全没有了昔日和堂兄弟霍斯特一争高下的气魄。
1989年5月,阿明·达斯勒和格尔德·达斯勒最终将其持有的彪马72%股份出售给瑞士企业Cosa Liebermann SA,至此达斯勒家族对彪马长达大半个世纪的掌控走向了终结。
1990年10月14日,六十一岁的阿明·达斯勒与世长辞。
很难说拱手让出彪马,对于这位矜矜业业一生为彪马的老爷子会没有影响,尤其是比起斗了一辈子的堂弟霍斯特,至少在临终之前看到了阿迪达斯已经在体育用品市场权倾天下的走势,阿明则得承受打上达斯勒家族失败的烙印,这种巨大的落差可想而知。
明面上看来,阿明和他的彪马是死于一次投资失败,死于与堂兄弟的争斗,但实际上早在1986年他作为世界体育用品工业联合会(WFSGI)主席在东京开会的时候,很多事就已经注定了。
当时,作为东道主Asics总裁鬼冢喜八郎手中,他为了撮合阿迪达斯的霍斯特和彪马的阿明共同坐在一张桌上,一起出席这个在日本召开的体育产业大会,实在是费了不少脑筋。
尽管最后这两堂兄弟并没有像他们的父辈那样,连死后坟墓都搬得远远的,还留下了一张非常经典共坐在一桌的照片,但他们谁也没想到,正是这位Asics总裁鬼冢喜八郎扶植过的美国年轻人菲尔·奈特,正在掀起体育用品市场一场新的巨头风暴。
阿明和霍斯特最终坐上了一张桌上
也就是在这场会议召开之时,耐克在美国的运动鞋销售份额已经达到了50%,而且趁着阿迪达斯和彪马在那几年进行换帅与交接之时,耐克「Just Do It」的广告语已经红遍了美国,红遍了华尔街交易市场。
不过此时阿迪达斯也已经远非达斯勒家族的阿迪达斯。在霍斯特去世后,阿迪达斯的达斯勒们也陷入了混乱当中。
也就在阿明·达斯勒去世前几个月,1990年世界杯决赛前发布会上,看上去又一次包揽了决赛两方德国和阿根廷赞助的阿迪达斯,谁都会觉得是等来了又一次营销大丰收,但谁也没想到一场关于阿迪达斯的巨大地震正从这场发布会蔓延开来。
一个叫伯纳德·塔皮的法国男人,竟然成了这场发布会的焦点。他说,「这是我一生中除了我孩子出生之外最美好的一天」。
塔皮成了阿迪达斯的掌舵人。就在发布会几天前,达斯勒家族决定卖掉他们所持有的80%阿迪达斯股份。
这件事后来被史称为「阿迪达斯案」,不仅是这位法国商人与达斯勒家族的纠葛,后续更是扯上了里昂信贷银行,而这桩扯皮的案子,竟然一直持续到塔皮在2021年去世,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桩世纪之案。
伯纳德·塔皮
一个运营了大半个世纪的巨型跨国公司,最终画上句号的方式居然是与一桩世纪之案牵扯在一起,这本身就不得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讽刺。
在达斯勒家族失去彪马之后也就不到四年,达斯勒家族再次彻底失去了阿迪达斯。
时代需要体育市场的商业模式走向新阶段,而家族模式自然成了被抛弃的过去,新的时代宠儿自然是落在了耐克等彼时的新品牌头上。
生命中曾经有过的所有喧嚣,都将用寂寞来偿还。
“特别声明:以上作品内容(包括在内的视频、图片或音频)为凤凰网旗下自媒体平台“大风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videos, pictures and audi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the user of Dafeng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mere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pac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