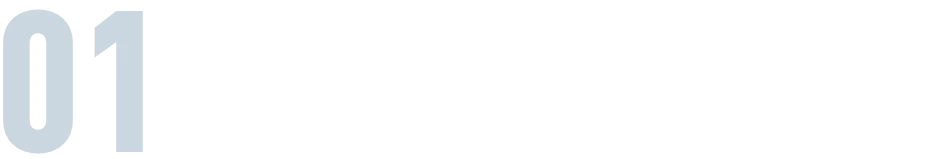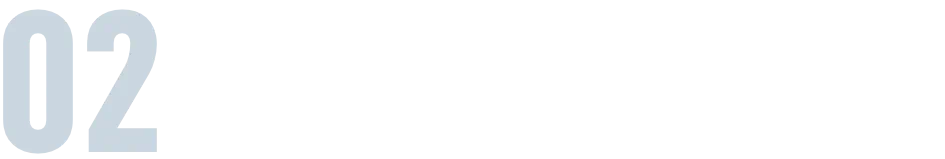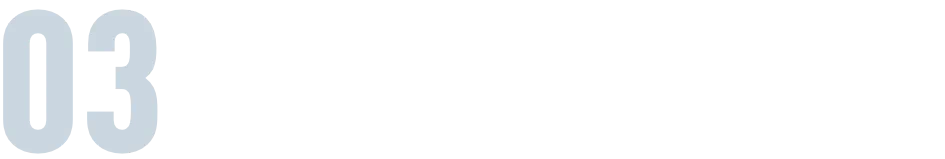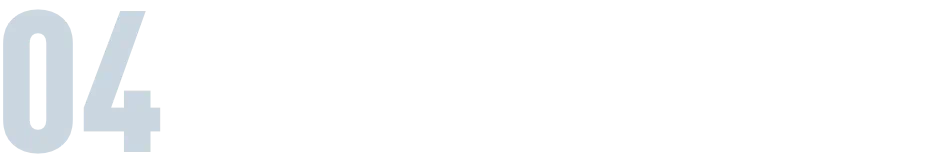一位中国记者,写欧洲问题,拿了国际大奖


独家抢先看
作者 | 沈天浩
【编者按】
5月14日凌晨,体坛传媒驻意大利记者沈天浩的作品《团结的欧洲杯,不团结的欧洲》荣膺国际体育记者协会2024年文字类最佳专栏奖。这是中国媒体第一次进入该协会年度文字类奖项的前三名,更是首度摘得桂冠。
这篇对欧洲杯的评论,也得到了欧洲人的认可。荷兰资深记者、评审团成员雅普·德·格鲁特评价道:“这正是我在2024年德国欧洲杯期间想说的东西,但即便是很多欧洲记者,也只把报道局限在了足球本身。事实上,足球就像是八爪鱼,它与社会的各个角落直接关联。”
这个奖项也证明了,哪怕是在足球领域,中国媒体也越来越容易被世界注意到了。
以下为获奖者沈天浩受邀为凤凰网《凰家看台》撰写的独家自述:
写作《团结的欧洲杯,不团结的欧洲》时,我还不知道AIPS的“最佳专栏奖”为何物,自然也不会考虑这个作品能够参评、获奖,在时隔近一年的今天被一次次重新阅读。
这并不是一篇精心构思的作品。2024年欧洲杯决赛前几个小时,我早早来到柏林奥林匹克球场,绕着这座庞大的混凝土建筑转了半圈,来到位于地下的媒体中心,心里想的是:“现在要写什么?”决赛当日,我的计划相当紧张:赛前要去到柏林市中心的球迷区,赛后还要参加发布会、提问题,并兼顾视频评述——每个小时都不能浪费。文字产出方面,比赛本身的现场稿自然是需要的,但除此以外,我还想写点东西。
简单想了一下。西班牙与英格兰的对决,就留给赛后的那篇现场稿吧;赛前准备的稿件,我想写即将落幕的欧洲杯,写过去一个多月的德国,写决赛的举办地柏林——这是个极其特别的城市。
关于柏林
近几年,我因为各种缘由去过好几次柏林:欧洲杯之前的两次,分别住在东边画廊附近嘈杂混乱的华沙大街,以及西边优雅克制以至于有些冷漠的夏洛滕堡;欧洲杯期间数次短驻德国首都,住过西柏林年轻人活跃的时髦街区腓特烈斯海恩,也和同事武一帆一起,拎着行李爬过东柏林得体整洁、但没有电梯的排楼。
◎柏林奥林匹克球场
人口300多万的柏林有着各种各样的街区,欧洲杯有着24支风格、气质、状态截然不同的球队。对我来说,二者同样有趣。佩措尔德的《温蒂妮》,也是我近年来最喜爱的电影之一,它的灵感来自欧洲古代的“水精灵”传说,影片开头女主在所供职的柏林城市博物馆里,为一组游客讲解战后柏林的样貌变更,人们纷纷看向我文中提到的城市模型——1945年之前和之后完成的建筑,以不同的颜色标注。通过这样清冷的画面,柏林的城市肌理与影中人物的情感神经,被巧妙地接在了一起。
“贫穷而性感”。2003年,柏林时任市长沃维赖特在接受杂志采访时,用这样一句话描述这座城市,而这也很快成了柏林的标签。柏林“性感”吗?当然。这体现在这座城市的夜店文化、穿衣风格和“不在乎”的性格。但性感的柏林,其实也是敏感的:在欧洲的主要城市中,它的历史绝对不算悠久,然而在最近200年的时间里,历史的几次转弯,将车辙留在了柏林的每一条街道上。柏林受伤、愈合、袒露伤痕,连同有着独特历史的奥林匹克球场,为“团结与分裂”的主题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场景。
关于德国
从欧洲杯前线回到米兰后,我经常在晚上躺在床上,回想起在德一个月的行迹,以及经历的种种瞬间。赛事报道安排的关系,我在好几座城市之间辗转,德铁app上记录的数据是:乘车32趟,去过17个车站,里程7381公里,在火车上总共待了2天20小时25分钟。
◎柏林的雨中彩虹
那些难忘的、特别的瞬间,其中很多就与火车有关。克罗地亚球迷在车厢里唱起歌来,场景起初非常温馨,但歌谣的主题很快变得敏感。在酒精的作用下,几个人的面颊已经泛红,他们笑着唱起“乌斯塔沙”,好像这不是一个极端主义组织的名称,而是邻居家宠物的绰号,或是达尔马提亚地区某种甜品的名称。这当然不正常。几天后,克罗地亚与阿尔巴尼亚的较量马上就要打响,汉堡的城际小火车不适时地陷入崩溃,我只得来到公交车站等车,见到了后来在文中提到、两国球迷合唱“科索沃”的场景。
有些瞬间,因为篇幅和时间所限,未能在文中分享出来。在多特蒙德,英格兰经由加时苦战,淘汰荷兰进军决赛。等到我参加完发布会、去过混采、折腾半天来到多特蒙德主火车站,时间已近三点,身边满是喝得半醉的英格兰球迷。几十公里外,武一帆在公寓里上了闹钟,等着给我开门,我想的自然是尽可能在回到住处前把稿子写完。好不容易挤上火车、抢到座位,我拿出笔记本电脑继续写稿,引来亢奋的英格兰球迷们围观。幸运的是,没有任何不好的场景发生。对面的球迷带着浓重的口音,坚持要塞给我一张球星“闪卡”。那张卡破除了我的一些刻板印象,现在夹在一本厚厚的《德国足球年鉴》中。
小组赛期间,我在莱比锡附近的哈雷住了一个星期,每天往返在公寓和火车站之间,前往莱比锡、柏林甚至汉堡。“人们变得越发冷漠,经济日益下行、社会矛盾尖锐”——在那篇获奖文章的末尾段落,我写了这样一句话,而哈雷正是我最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现象的地方。除了德国队赢球的夜晚,从火车站到市中心的10分钟路程,总是寂静、冷清、压抑的。
◎沈天浩镜头下的火车站
哈雷也是德国人均收入最低的主要城市之一,而在我离开这里整整七个月之后,这里突然登上了全球媒体的主要版面:德国选择党在此召开的集会上,马斯克以视频电话的形式出现在了大屏幕上。2月,德国进行大选,地图上的颜色分界线,与1989年之前的两德国界几无二致。《团结的欧洲杯,不团结的欧洲》里,我写施普雷河畔的东德博物馆,那里访客络绎不绝,展览设计的互动性很强,但讲述的似乎不只是历史。
关于欧洲
柏林奥林匹克的城际火车站和球场之间有一小段路,那个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成为获奖文章引子的“因足球团结,团聚在欧洲之心”,就贴在那段路旁的一个铁栅栏上。对“团结”的呼吁和向往,对“分裂”的关注和恐惧,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欧洲每天正在面对的真实。
AIPS评审团成员、资深荷兰记者雅普·德·格鲁特的比喻“足球就像八爪鱼”,得到了不少人的共鸣。颁奖现场,我和他聊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欧洲杯期间,荷兰球迷们的狂热和装束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们的民族意识其实相对很弱,却十分热爱自己的国家队;反过来,意大利人的民族意识在欧洲出了名的高,可很多意大利人其实并不在乎国家队,甚至会为影响俱乐部比赛的蓝衣军团喝倒彩。为什么会这样?
◎露天下观赛的球迷们
当然,足球从来不只是一项运动本身。它是这个世界的一面镜子,可这镜子有时擦得并不干净,有时是扭曲形象的哈哈镜,有时则是自带背光美颜的浴室化妆镜。也正是因此,我试图通过叙述足球去触及社会,不过仅此而已。足球无法忠实地反映出社会的全貌,更无法解决社会的所有问题。
但足球至少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轻盈、快乐、有希望的出口。足球世界的2024年欧洲杯上,团结的西班牙和英格兰杀进了决赛,团结的瑞士和奥地利创造了惊喜,不团结的意大利队成了反面典型;足球以外的现实里,“团结”与“不团结”的边界往往要模糊得多,有些“不团结”的姿态,是为了在更小范围内达成更紧密的团结。有着移民背景的亚马尔、威廉斯,以及在海外联赛效力的罗德里、鲁伊斯等人,为斗牛士军团带来冠军;可对于欧洲社会上的绝大多数职业而言,外来户和移民想要顺利融入、被认可以至出人头地,成功率比职业球员要低得多。
关于写作
说到“普通人”和职业球员的对比,我的确很感激这次获奖的机遇——它让我在很短的时间周期里,体会到了球员生涯式的递进成就与刺激感。起初AIPS通知全球媒体参评,我把这篇文章交了上去,但当时对奖项的评选过程不甚清楚,对最终的结果更是完全没有预期。说实话,最初提交作品的时候,我根本没有进行全文翻译,只是附上了一段英文的文章摘要。原因很简单:怕的就是耗费心力做了全文翻译,结果投稿“石沉大海”——找工作投过简历的人,肯定明白那种感觉。
提交作品是在去年10月,此后很久都没有收到消息,我偶尔想起过这件事,心想有可能确实没下文了——事实证明:我只是对流程太不熟悉。直到今年3月中旬,我突然收到邮件,发现AIPS开始陆续公布各个奖项的入围名单了。在最佳专栏奖公布入围名单的新闻页上,我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和作品:“Tianhao Shen (China), A United Euro 2024, an Ununited Europe - Titan Sports”。
◎沈天浩与奖杯合影
在此之后,那行字还出现在候选名单、前10和前3的名单上,希望的火苗燃烧得比想象中更久。骆明老师和体坛国际足球编辑部的同事们,一直对我充满信心,比我更相信这篇文章可以走得很远——这种信任和支持,连同读者们对我的祝福,伴随着奖项的整个评选过程,放大了我的感动与喜悦。
我本人倒是每一次都做好了出局的心理准备:倒不是因为觉得自己写的不够好,而是真的不知道它在国际评委们的眼中是怎样的。更何况,2024年度的各大奖项评选,AIPS收到了来自136个国家的2065份候选作品,是为史上最多,竞争激烈程度不言而喻。
前几轮的晋级名单,是通过邮件+网页新闻的形式更新的,但通知我作品进入前3名的,其实是一通电话。当时我正在录制播客,同事小五开玩笑:“这是个《法国足球》式的电话!”他们邀请金球奖候选人出席颁奖典礼,也是靠打电话。组委会告诉我,他们此前在评选中看的一直是我文章的机翻版本,然而现在决赛在即,需要我提供一份作品的“官方”英文翻译。
骆明老师得知此事马上预言:“我觉得你很有机会夺冠!”结果准确,可我想来其实有点后怕:如果这篇文章确实具备夺冠的可能性,却因为翻译的质量问题被拒之门外,那多令人遗憾?做事情果然还要全力以赴。即便起初试着不把这个奖项太当回事,但在真的进入前三名且得知最终结果会在颁奖典礼现场告知的时候,我不可避免地变得“在乎”了。
我一直觉得,选择成为足球记者,意味着接受在足球叙述中成为旁白或配角的宿命——那些精彩的故事、个人英雄主义的魅力、强烈的悲喜瞬间,通常属于聚光灯下的球员们。此番来到拉巴特参加颁奖,宣布结果的那几十秒钟,我感觉自己像个把命运寄托在点球轮盘赌的球员。这是强烈而真实的、不是所有同行都能有机会体验的感受。我是幸运的。
◎沈天浩发表获奖感言
那的确像是一场12码决战。常言“文无第一”,本次入围“决赛”的另外两篇候选,分别关于法国罩袍禁令的社会争议,以及洛杉矶奥运会板球场地变更的幕后故事,那是和我的文章类型风格完全不同的优秀作品。这一次,我赢了这场“点球大战”,或许得感谢佩措尔德的电影、柏林的伤痕和德铁车厢里的故事,以及文章中倾注的那点悲观的感性。它以希望开篇,但后调毫无疑问是沉郁的。
敲完《团结的欧洲杯,不团结的欧洲》的最后一个字时,场景已经更换到了柏林东南郊的酒店房间。我有在电脑里保存稿件的习惯,那个文件的最后修改时间是:2024年7月15日,3点49分。交稿后未再改动。足球媒体通常这样描述点球赢家:“幸运女神向我微笑。”将微笑放在一边,如果一定要找一个“我值得”的理由,大概就是“体坛”文件夹里最后修改时间一列中,那些日期后面以“2”“3”“4”开头的数字。这是很多文字记者们的共同记忆,衷心希望中国文字媒体在AIPS年度奖项中取得的这个突破,能够激励我们一起继续下去,做真实、有温度、负责任的表达者。
作者 沈天浩
“特别声明:以上作品内容(包括在内的视频、图片或音频)为凤凰网旗下自媒体平台“大风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videos, pictures and audi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the user of Dafeng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mere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pace services.”